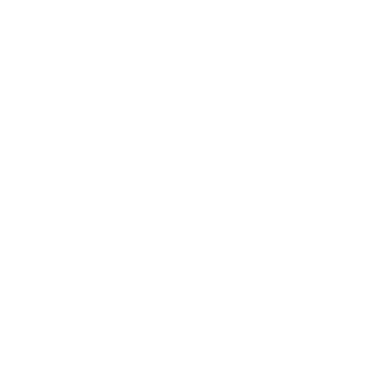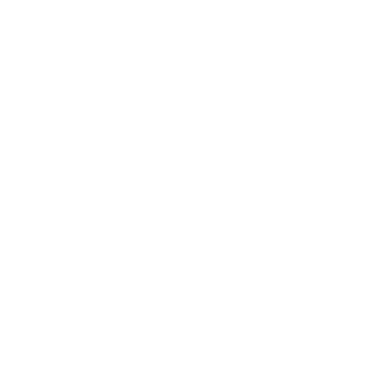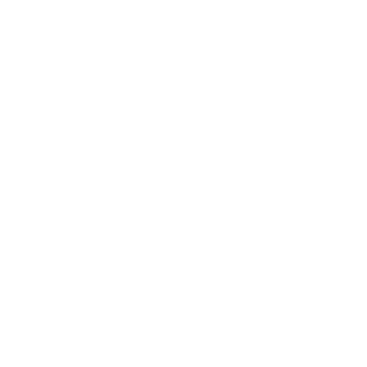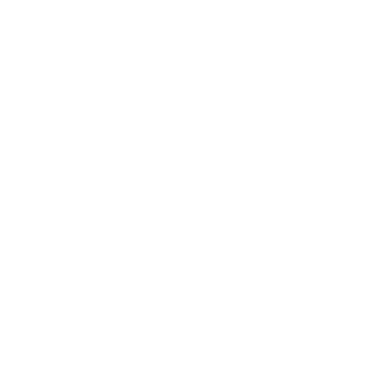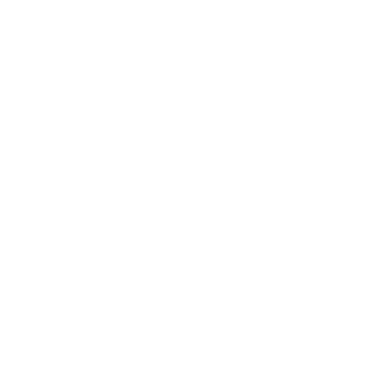我就是个老套的洛杉矶人。我度过了一个保守的、受控制的童年,之后又过着尽我所能不受控制的生活,再之后才发现原来我是喜欢被控制的。我的故事也是我这代人的故事:孩子们受到太多约束,长大后变成瘾君子和酒鬼,最后在精神灵性与禅宗里找到自我。太常见了。我就是个常见的人。
还是个孩子的时候,我挺女孩儿气也挺敏感的。还是那个老套故事:小镇里的敏感男孩,试着融入周围。我几乎时时刻刻都感觉受到威胁。成长过程中,人要怎么表现,外界总会有某套特定的规则和期待。我总是为此愤怒,然后就很想报复。我也试着去符合这些规范,但老是不太成功。我被迫低了头,用自己感到不舒服的方式做事。他们这些规则不见得公平。这些规则束缚人、拉紧人,没有任何意义。我还必须得表现得阳刚一点,不能变得华丽或是热烈,我必须得男人一点。这是很羞辱人的事。这在某种程度上培养了我敢于违抗与叛逆的性格。当我孤身一人来到大城市里的艺术学校,我就尽可能地华丽和热烈了。
我生活在洛杉矶铁路边上的一间仓库里,得爬梯子进去。我那时的车还有鳍状车尾。我穿的是厚底靴和大斗篷,化全妆,戴着手套上床睡觉。那时候,如果要回波特维尔(Porterville)看我爸妈,我就卸掉全部妆,擦掉指甲油,穿上普通衣服。我回家看望他们,再去挑衅他们有什么意思呢?如果我要和他们保持关系,我就得妥协。这不是什么坏事。再过后几年,当我与他们完全坦诚了,允许他们走进我的生活了,他们也得做出妥协。这挺好的。某种程度上,他们改变对我的看法,是因为钱吧(哈哈哈)。我爸妈后来觉得,只要还是这么成功,那他肯定不会出问题的。真是苦涩的甜蜜,因为这明显不是个正确的因果逻辑。但生活总不是完美的。
我总是想要参加到这个世界中去,去参与点什么。再年轻一点的时候,我很胆小,而且总是不太能融入进去,所以我借助酒精壮胆。但我总能找到某种方式与这个世界进行沟通。我向人们呈现一份我对世界的想法,不是想要强迫他们接受,也不是想坚持什么。这不是什么宣言(Manifesto),只是我的想法。应该是很温和的。尽管这脱胎于我对自己身上被强加的规则作出的反应,我希望这只是其中一种方案,不是唯一的选择。对我来说,这很重要。
我喜欢人工精心制造出来的假象。我说的不是唇膏或是肉毒杆菌,而是对想法进行夸张与强化,而不是努力想看起来年轻。想想歌舞伎,想想一个房间里什么都没有,只有墙上一幅卷轴画,一盆插花。还有茶道,精心伪造与庄重仪式的成分一样多。好吧,可能这和唇膏或肉毒杆菌也没什么差别——我不想变成那种声称知道其中规则何在的人啦。我也不希望自己听起来像是个固执己见的人,虽然我可能还真是这样的人。我喜欢的那种精心伪造是夸张的,带有暧昧的滑稽。要能挑战所谓的“好品味”与传统审美观,但要以一种幽默的方式。你知道的,幽默正是全宇宙里最优雅的东西之一。
最成功的男装,应该是保守内敛,再加上一点点叛逆就好。
我是个将原本的灰色卷发染成黑色长直发的55岁男人。我是个已经坚持去健身房20年的55岁的男人。我用激素与健身,用计算精准的方式来改造我的身体。最开始去健身房,因为那时酒喝得太多了,要平衡一下,还因为我希望改变自己的身体。我不太满意我身体原来的样子。我的太太(Michele Lamy)也经常去健身房,所以她也开始逼着我去。这就和我每天刷牙一样规律了,就是一件做了能让我感觉“对”的事情。一种打理自己身体的习惯。我不是说我的体型是完美的,但我的身体达到了我想要的完美程度。我不需要用衣服来遮掩身体的缺陷,让自己变得比实际好看。我现在也对我女性化的一面十分自在了。我绝对是个老“皇后”。
我不觉得我的衣服很激进,但可能对我这样年纪的人来说,还做这样的衣服有点好笑吧。我穿衣服的选择,与我生活的方式与我需要去做的事是逻辑一致的。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每天需要借助穿衣来表达的,所以这些打扮也算是我的制服吧。同一件衣服我可能会买个20件,我穿自己设计的球鞋。
话说因为球鞋设计我变得很出名,这有点讽刺。因为最开始做球鞋,是因为我想做一个滑稽版,去取笑球鞋。我觉得球鞋是地球上最无聊的东西,完全是“平庸”的代名词。但还得去健身房啊,必须得穿球鞋,所以我就开始做一些带有我自己夸张风格的球鞋,之后这就变成我的标志了,现在是我卖得最好的东西。
我现在穿的这双球鞋,上面接有一对弹性皮革袜,有点像一只球鞋上长了一只歌剧手套。我还穿了稍微过膝的口袋短裤,然后这个袜子球鞋拉起来正好盖过我的膝盖。因为我还是觉得要把自己毛茸茸的小腿完全裸露出来有点粗鲁。遮起来比较谨慎一点吧。我还穿了一件丝质针织工装背心,黑色高领开司米毛衣。去健身房的话,我脱掉毛衣,把袜子往下拉一点,这就是我的运动装备了。我不做什么心肺适能类的运动,就是举铁和拉伸,所以也不太出汗。特别实用。
{page_break}我的短裤明显也是参照滑板手的装备的,或者是洛杉矶八零年代的墨西哥帮派风格,也可以说是参照佛教徒什么的。黑色高领毛衣可以解读为对60年代“垮掉的一代”的精神家园——巴黎圣日耳曼:建筑化风格,正式,严苛。在这外面我经常是套一件黑色尼龙飞行员夹克,部分是因为Montana在80年代老爱穿这个,而且如果穿皮夹克我会觉得太重。工装背心没什么特别的含义了。
简单来说,我就是个爱穿短裤配跑鞋、戴晚装手套的55岁的男人,估计其他55岁的男人不会觉得这是梦想装束吧(哈哈哈)。但不管什么样,我已经把自己弄成一位巴黎设计师了,巴黎设计师总是让人期待会有些古怪的审美吧。要是我哪天穿了身西装,大家会很失望的啊。
我对衣服其实真没什么兴趣,我自己是这样的。我不买衣服。你知道的,建筑大师让-米歇尔·弗兰克(Jean-Michel Frank),衣柜里有40套一模一样的灰色法兰绒西装。我一直认为这在中庸与夸张上同时达到了一个高度,我很喜欢。忘记什么时候开始穿我这套“制服”了,时间也挺久的了。90年代那会儿,我在运动裤外面穿军备短裤,上身穿T恤和皮革外套,也穿了挺长一段时间,可能一直穿到我来巴黎吧。到了巴黎,我开始穿缀有黑貂毛的皮革外套,还是会穿军备短裤。慢慢就变成我今天穿的样子了。我好几年都穿同一套衣服,隔几年再做点改变。当我看到有人总在改变自己的风格,我就想问了:是不是你不了解自己呢?我也不是要批评谁,我是很真诚想问他们。
我去哪儿都能穿这套制服,不管是会去听歌剧还是参加锐舞派对。除非是要表达敬重,很少有什么场合我会专门改的。今年我去参加了白宫国宴,还是穿着我的短裤和球鞋,但是外套换成了黑色女公爵缎西服外套,加了一件黑色高领丝绸上衣。我不想表现得粗鲁。我希望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,但要到别人家里做客,我会对主人想营造的氛围表示尊重。待人有礼比公然反抗重要多了。我不希望让别人感到不舒服。我已经在自己的发布会上展示了裸体啊还有其它奇怪玩意儿,因为时装发布会是一个复杂且追求极致的美学竞技场,人们期待在这个竞技场上看到某种带着惊奇和挑战的元素。我不会为母亲的教堂小组弄这样的走秀发布会。这是不礼貌的。
据世界服装鞋帽网了解,最成功的男装,应该是保守内敛,再加上一点点叛逆就够了。想象一下,某件经典款单品,带有被撕裂的内衬或是象征虐恋意味的绑带。这是各家商店卖得最好的。我自己也会做这样的东西。这是男装发展的有趣时期。很通俗,又很受限制。现在的我们太拘谨了。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时装天桥不弄得更夸张一点——可能华丽热烈的东西已经走到尽头了吧。
尼尔·杨(Neil Young)是我男装设计的灵感来源之一。他从来没兴趣打扮。他是诗人,带有阳刚气质,但是又那么敏感。他看起来很诚恳,又带有一点幽默。女人幽不幽默应该不是最重要吧,但绝对是令一个男人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。我们的期望是,男人建起房屋,女人将房屋变成了家。这实在是一种很具原始意味的想法:我们仍旧希望男人提供物质基础,女人增添优雅慈悲。
时装之所以受欢迎,也是因为神秘。这是我们作为设计师,展示的一种意见,包含了微妙事物里的起起伏伏,人们的回应,就像是天空中的飞翔的群鸟,突然集体调头往另一个方向飞。这就是其中令人着迷的地方,关乎那些某些人在某种模糊程度上理解到的直觉和微妙参照。这是一种,能让一群人在同一时间领悟的图案或是密码。
作为一名设计师,你必须得尽可能地改变,来维持人们对你的兴趣,但又不能改变得太多,变得不真诚。要实现这种平衡没那么简单。我很好奇什么时候,我不再理解对这个世界相关的事物,还继续完善一个不再重要的愿景。我们曾经见过这样的时刻到来,这样的时刻降临到我身上,我害怕那天的到来。
我父亲今年去世了,所以这段时间我对死亡想了很多。他喜欢挑衅,又很喜欢分析。他喜欢在脑力上把人逼到无可后退的角落——这也算是欺负人吧。他总爱批判别人的生活方式,到了最后变得很苦涩。我想了很多年,但从来没机会问他为什么,为什么他还是不能找到平静。关于生命的结束,他没能用优雅的方式去谈判。他洞穿真相,坚信要做一个意志坚定的人——做一个能够正确思考的人,但他还是不能平心静气接受自己正在死去这一事实。
这让我开始思考这个世界,思考应当如何找到优雅的方式去面对各种威胁。这是我想做的。我希望自己的生命结束在一个四面有墙的花园里,我读着书,和小猫咪玩耍。这可能是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死法了。我不想要孙子孙女。嗯,我想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的身边应该会有不少人,他们会想要小孩。我也喜欢身边有小小的婴儿。好吧,那么我希望最后能够很舒服地呆在那个花园里,逗逗小猫咪和小婴儿。我真的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。
更多精彩报道,请关注世界服装鞋帽网。
❥发表您对此文章的看法,点击下面⇩ 【热门跟帖】
热门跟帖✎
◆世界服装鞋帽网版权与免责声明
查看全部↓